万物皆流,万物皆变。在“流变”一词广泛应用的当今世界,究竟什么是流变学?其在科学殿堂中的地位如何?它在今天和将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带着一系列问题,我们采访了我国流变学领域的初创骨干,耕耘至今的著名学者许元泽教授。

2009春,驾车自沪南下厦大,途经太姥山
《科学中国人》:流变学这一诞生于20世纪的科研领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广泛应用于材料科技领域。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流变学的发展线索及其意义。
许元泽:对流变学的理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流变概念类似变化之道,这种哲理,古已有之,我国先秦诸家和犹太希腊先贤各有天才论述。现代流变学作为精确物理科学来讲,是研究复杂物质的流动与形变的科学。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天然与合成高分子、玻璃、金属等工业材料,岩土、石油、矿物等地质材料,血肉脏腑等生物材料的性质中,发现经典弹性固体和牛顿流体理论不能说明这些材料的复杂力学特性。应用呼唤著科学,但一门科学不光有对象,也要有精确的内涵与独特的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流变学发端于19世纪时为现代物理学奠基的麦克斯韦和玻尔兹曼等的工作,他们提出了力学量表达的时间依赖性方程,流变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精确科学的特点。流变学名词(Rheology)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自那时起,一批土木工程师、高分子与胶体化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际体系的流变学实验研究和理论模型的概括,同时,一些理性力学家建立了宏观连续介质本构理论的公理式结构;60年代,宏观流变学体系已基本确立; 70年代的研究主流是寻找流变学本构方程,使其能够尽好地定量描述实际物质在各种形变下的流变响应或称物料函数,采用各种流变模型的软件开始用于高分子加工。但是宏观方程往往顾此失彼,不尽人意。上世纪下叶逐步认识到单一宏观尺度理论难以描述的这种复杂性,源于化学物质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尺度结构与相互作用产生的复杂松弛过程。因此,深入物理化学微观本质十分关键,我们称之为结构流变学。早在五六十年代,高分子物理学家建立了大分子链的熵弹性和松弛特性的定量联系,但包括链缠结和多相界面体系尚未突破。近二三十年凝聚态物理突破性发展,尤其是其中以法国的诺贝尔奖得主de Gennes教授为代表的软物质物理的兴起,给复杂流体流变学以新的思想和方法,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多尺度物理的介入还将主导今后一段时间流变学领域的发展。流变学这一介于物理、力学、化学之间的学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地体现交叉科学本质。它的责任也越来越大。对象大至石油开发、土木化工,高到空天材料,近到衣食住行离不了的合成与天然高分子及胶体分散体系,小至生命科学、微电子信息和纳米科技等前沿领域的众多复杂物质。尤应强调的是,广泛材料的加工态往往也都是复杂流体。物质结构与流动形变特性的千变万化亟需统一的理性的认识和分析方法,它应该成为材料科学家与过程工程师进行创新的重要武器和科学思维的基础。不过我们离这一目标还可谓任重道远。然而,缺乏流变学知识的教训已不胜枚举,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由于在低温下助推火箭的密封橡胶弹性恢复力不够,燃料泄漏而机毁人亡;雨水渗入地层引起的屈服和蠕变导致大楼倒塌和众多泥石流惨剧,等等。如果能予作流变学分析能否避免呢?
《科学中国人》:您是如何走进这一领域的?这一学科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许元泽:在大学时尚无这个专业,我是从高分子物理学方向逐步接触流变学的。今年,正是我进入中国科技大学高分子物理专业50年,该专业1958年国内首创。其设计者钱人元教授是我国高分子物理学主要创始人之一,精通物理化学与实验物理。1964年,我考入中科院化学所钱人元教授的实验室,成为他的研究生,题目有关粘弹波——高分子防弹玻璃的作用机理。其实,我开始做高分子粘弹性研究最早是由吴人洁教授指导的本科毕业论文——环氧树脂的应力松弛和化学松弛。文革时期学业中断,我们下厂 “抓革命,促生产”避免荒废科研。钱先生当时“下放”我们组,指导聚丙烯棉型纤维熔融纺丝工业化的任务。我们购买了毛细管流变仪,自制熔体落球粘度计,开始熔体流变学的研究。流变分析发现少量的高分子量尾端在纺丝流中决定着大分子的取向结晶以致纺丝成败。这一思想推动了聚丙烯棉型纤维工业化的成功,赢得国内国际大奖。那段时间可算是初探流变学。
不久,德国洪堡基金会来华选拔访问学者。我去了亚琛技术大学力学工程系休谟(P.Schuemmer)教授实验室,他是国际著名研究粘弹连续介质力学的学者,数理功底很深。我在亚琛技术大学的研究题目是高分子溶液的结构流变学本构方程及其在收敛流动中的应用,这一工作使得从高分子链结构全面定量预测稀溶液宏观流变行为成为可能,从分子水平诠释了大分子动态行为的标度规律。该工作使我两年得到博士学位,并获得亚琛大学金奖。这段工作加上大量阅读使我对流变学规律之奥妙有了整体概念,也弥补了一些数理知识的缺陷,增强了我钻研流变学领域的信心。

1981年,许元泽教授与钱人元先生在德国Freiburg一同探讨流变学问题
《科学中国人》:您后来为什么选择回国呢?那时候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环境比不上国外,您回国后如何开展工作的?
许元泽:1981年秋博士毕业后,休谟教授曾推荐我继续去美国发展,但化学所柳大纲所长和钱先生希望我回所主持发展流变学的工作,那时候的思想觉得留在外国是不忠,回国没有什么犹豫,回国四年后一家四口还挤在一小间筒子楼,楼道里做饭,也没觉得太苦,因为同龄人都这样。再说出国前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制定科学规划,决定在化学和力学规划中积极发展流变学,我参加了湘潭大学袁龙蔚教授主持的流变学发展规划的起草。对发展我国流变学的意义和责任也有一定认识。
回化学所以后十年工作,主要三方面:承担国家有关重大任务和工业项目;建设流变学实验室,发展学科;建立中国流变学会。

1988年,许元泽与国际流变研究领域著名专家de Gennes教授合影
事实上当时发展流变学的社会理解和经费支持都缺乏。要积极寻找项目,“任务养学科”,购买流变仪,再从项目经费中逐年还清,近十年建设起了初具规模的实验室。当时的情势决定工作的路数是从技术问题的需要出发,寻找里面关键的有关基础科学问题的答案,切实带动技术的进步,针对性地也发展基础科学。这慢慢成了我多年科研的模式。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复杂流体结构流变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研究复杂流体流变性质与流体多尺度结构的关系。研究过的对象其实是通过一项项科技任务串起来的。高分子溶液的基金项目与三次采油国家攻关项目结合,解决高分子驱油机理;通过熔体流变学研究发现纺丝和塑料加工中分子量分布调节的重要性;中科院重大项目顺丁橡胶国产化中,我们发现生胶长支链支化对加工的关键影响,有利于改进聚合反应;这些项目都得到国家级奖。还主持了电流变体研究以实现机电一体化的重大基金项目;参加钱先生主持的高分子凝聚态重大基金项目中液晶高分子流变学等。八十年代部份基础研究的心得反映在我著的“高分子结构流变学”一书中。此外,在访加、美期间为发展高性能复合材料研究复合体系流变方程,为新型水基涂料开发研究悬浮体与乳液流变学,等等。这些经历使我接触广泛复杂流体,对基础科学与工业应用关系也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本世纪初蒙复旦大学杨玉良教授举荐,回国任教复旦大学高分子系,继续研究复杂流体。他和他的团队在高分子凝聚态物理方面的出色工作对我很有启发。近年来我在一些重大项目中努力用多尺度凝聚态物理学的方法来解决一些材料科学过程流变学方面的关键问题,例如973项目北京航材院益小苏教授提出通过热固性树脂与工程塑料离位共混增韧制备结构复合材料的方法。我们对热固-热塑体系固化反应相分离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使得控制形貌的优化加工设计成为可能。这样的例子还有有关共混体系的重大基金项目,有关火箭含能浆体流变学的973项目;中石化三次采油的弱凝胶驱油项目等。这种以多尺度物理发展材料工程的努力还只是开始,方兴未艾,反映了今后先进材料科学与过程工程中智能设计和虚拟加工先行的发展方向。这里丝毫不忽略实验,而要加强在理论思维指导下的各尺度实验,否则数学模拟也会脱离实际而走偏。
《科学中国人》:您的研究兼顾了发展基础科学和促进技术进步,这是国家极力号召的,这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您在国内科研多年,也曾先后在德国、加拿大和美国担任客座学者,并且在跨国企业中从事过科技研发。您能否结合自己的体会,谈谈对待发展基础科学和促进技术进步,要防止那些盲目性?
许元泽:我们年轻时代国内人文物质条件都不易搞基础科学。我自己多年来都是匆匆完成科研任务,一旦问题解决,文章也顾不上写,兴趣和压力转移到下一问题,虽有大量工作报告,只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已属不易。自觉基础研究搞得不深不透。现在国内领导重视科学,经济发达,重点院校硬件经费条件不逊于国外,但大家还感做学问难,压力大,出不了大家,等等。我觉得一些观念和管理上需要改进。要认识科学与技术的差异性。基础科学是人类求知,是开辟思路,评价时应重方法的创新,不能急于求成,太强调效益;而技术则要达到设计的结果,更强调组织管理与经济效益,用技术管理对待科学,往往效果不佳。对科学人更应有一种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靠“百家争鸣”解决学术问题,避免过度组织管理和名利激励。像国外允许一个教授多年坚持一个小领域,追求完善,各人都有学科强项,国家就是科学强国。古人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为什么?各有所长,互敬互学;低水平差不多的人易重复,难合作,矛盾多,上面压力再大一点,下九流做法就出来了,更难创水平。在国内要取得科研事业的成功需要更全面为人处事的素质与性格上的坚韧,这对一些科研尖子不免是苛求。真不希望我们孩子从小生活在人际竞争的压力下,变得机敏平庸,磨掉了对科学的由衷热爱。只要减少干扰,避免浮躁,科研环境就好,有那么多青年才俊潜心钻研,科学发达与技术的进步是必然的,明星不靠刻意捧也会冒出来,海外有志人才不赏重金也会回来。
几十年来,我与国内外材料工业技术界接触频繁,他们对科学家与技术结合方面有些看法。科学要为技术服务,技术是直接生产力,更关国力。其实技术更难,因为一个技术问题的解决总是需要满足多种因素和指标,如果科研不在关键指标上攻关,退而在次要因素上做文章,不能说没有创新,但却有避重就轻之嫌。科学家应该把最好最新的科学成就和困难实事求是地贡献给工业技术界,让技术界出成果。若科技评价失衡,出文章压力也影响工业部门科研机构人员升级考核,技术问题做走样。一些国家投资甚多的重大科技项目,往往也分了钱各人解决自己压力,总体效果不佳。国外则有不同的问题,本来科技工业界有自主研究传统,跨国公司的中心实验室能吸收最优秀的人才,配备最先进的设备,提供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人才无后顾之忧,全力发展技术。但近十多年以来金融资本追求利润的疯狂,用短期眼光来对待不同成长率的企业,使产业资本恐慌,成长率一般的化工、材料、高分子等产业也受到很大伤害,自然殃及长程研发,工业基础研究纷纷下马,人员失业转向,削弱了原创研究。最后,预料之中的全球经济危机终于爆发。沉重打击工业界,复苏科技尚需较长时日。我们要抓住难逢机会以科技进步改造经济,占领制高点,就要去除我们自己的盲目性,警惕国外的教训。一言以蔽之,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按科学与技术的内在规律做事,以广大科学中国人为本。

1987年许元泽与陈文芳两位教授一同在成都参加学术交流期间合影留念
《科学中国人》:您是我国流变学界的元老了,能否介绍我国流变学会是如何成长的,多年来有什么经验可供现在流变学界借鉴的?请结合您的经历给我们分析一下我国流变学发展的优势和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何在流变学的未来的发展中走到国际前沿?
许元泽:我国流变学会是在科学的春天诞生的。前面提到科学大会已有规划,说明也有一定工作基础,分散在各行业的流变学同行有强烈交流愿望,1980年英国流变学家陈文芳博士受聘北京大学力学系教授,他开设的具有国际水平的非牛顿力学讲习班,使国内分散的流变学工作者有机会聚在一起,其中几位同志后来成了中国流变学会初创时期的骨干。1981年我回国后与陈先生有很密切的科研合作。我们串联了一些优秀人才,在中国化学会理事长钱人元先生和中国力学学会周光炯先生大力支持下,中国化学会和中国力学学会决定成立直属两会的二级学会流变学专业委员会。按传统应由德高望重的影响力大的学术权威,例如钱先生和周先生领导,考虑到新兴交叉学科的特点,两位老先生高风亮节,破格支持让第一线搞流变学的外籍专家陈文芳教授担任主任委员,湘潭大学袁龙蔚教授担任副主任委员,由我担任秘书长,中科院化学所为挂靠单位。1985年在长沙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流变学学术会议,宣布成立流变学专业委员会。来自流体、固体、地质力学,化工、高分子等领域的委员们团结奋斗,八十年代在国内外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几年内流变学会会员增至近300人,领域广泛。并于1987年成为国际流变学协会成员,主办世界流变学大会“申奥”差一点没成功。八十年代的初始辉煌中,逐渐也表现出后劲不足。一方面,我国的流变学起步较晚,多年来的国家投入很少,我后来也担任过流变学会主任委员,感到不像国外,国内以流变学名义难以申请到资助,缺乏实验室建设积累。更重要是人才不足,这门学科是新兴交叉学科。具备扎实深厚多学科基础青年人才缺乏。一晃眼,二十年过去,国家大变样,现在是新的一代领导流变学界,我无法在此对近年来国内流变学界现状作综合评价,从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好的学会,要由本学科的最优秀最热心的人才组成,作为交流争鸣,团结协作的舞台,对学科发展可以起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否则就不能吸引各方智者投身这一领域,学会也容易边缘化,高水平的队伍散到临近学科。我以年近耳顺之年回国工作,只能在流变学领域继续针对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尽微薄之力。除了前述注重物理学与流变学的结合的研究项目,主要是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交流和人才培养。2005年,我国流变委员会在上海主办了第四届太平洋地区流变学国际会议,我并同美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流变学家Macosko教授合作主办国际复杂流体研讨班。他认为,这样的流变学研讨班是具备国际水准的。现在,基本上每两年由上海交通大学流变学研究所举行流变学研讨班,2009年的会议参加者竟有200人之多,令人十分鼓舞。我国的流变学发展从八十年代开始就有比国外对象广泛的特点,只要各方人才潜心钻研,发展出一系列的特色方法,再加强交流,互相借鉴,应能加强深度,提高水平,形成我们自身的优势。当前,国内大学和科学院下大力气积极引进年轻才俊,建设软物质物理,新材料科学与新过程工程的智能设计实验室,大量企业单位重视制品创新,建设流变学实验室,这将为流变学发展再创辉煌。
我认为人才培养的难点是一门交叉学科同时需要具备不同二级学科的背景。在我看来,当前的教育体系还不够灵活,专业考试科目限制了交叉学科学生的入学,不像国外教授有较大的自主权。造成学生思维往往局限,学数学和物理的学生,往往不易面对复杂化学物质的结构和相互作用;学化学的学生虽然也学过高等数学与普通物理课程,但因缺乏应用层面的训练,久而久之对学过的数理课程产生了疏离感。其实,掌握流变学需要补的数理基础并不是很多,尤其在信息时代,数理方法软件化,市场化,便于材料、化工的学生大胆地闯进这个领域。一个好的流变学者也应该使理论与实验融合。不能因为不懂理论而搞实验,也不能因为做不了实验就只搞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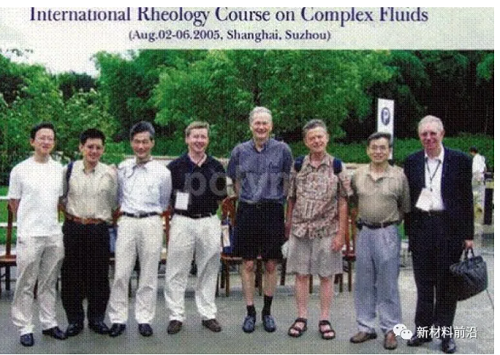
2005年,许元泽参加了复杂流体研讨班并与教员们一起合影留念
《科学中国人》:感谢许老师结合自己在国内外多年从事流变学和高分子科技研发的经验体会和丰富阅历,对我国流变学发展,以致更普遍的科技教育提出了自己的关切,很受启发。我注意到您现在也是厦门大学教授,能否在结束采访前谈点今后打算?
许元泽:我书生一世,孔夫子没学好,也不善经营,但一句话“学而不倦,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倒是实践的。厦大化学化工学院声名卓著,我有幸被聘为教授,来物色英才,培养后俊,发展高分子学科,结合该校该院各优势学科,同复旦大学和国内外各院校加强交流,共创高分子和流变学的新天地。

